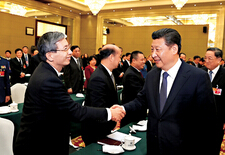曾钰成:我的父亲──怀念父亲曾照勤逝世十周年(上)

图:1966年摄于香港大学宿舍开放日。前排左起:妈妈、嬷嬷、妹妹。后排左起:友人、五伯父、钰成、德成
编者按
这是一篇充满感情、值得细读的好文章。
文中主角、前中华总商会秘书曾照勤先生,和多少上世纪中叶的小市民一样,自己早出晚归、辛勤工作,为的就是子女成材、出人头地,改善全家人生活。比很多人幸运,他有三名读书成绩优异又“听教听话”的子女,“老两口”的美好“安排”是:聪明的长子钰成当数学家、内向的次子德成当医生、三女励予最小也是个高级行政人员。
然而,一场“五月风暴”,惊醒了三名年轻人炽热的心,也惊破了这位严父的美梦:德成、励予兄妹因同情工人学生被捕入狱,钰成放弃了几份美国一流大学的奖学金去培侨中学教书。
在父亲生前,基于各种原因,曾钰成大概没有向父亲说过什么感激的说话,今天,就是在这篇纪念文章里,曾钰成仍然颇“吝于”各种感念赞颂之词。但是,父亲一生做人做事尽心尽责、刚正不阿,一辈子情繫家国对子女带来影响,以及子女因此而对父亲产生的无尽感激与思念,在这篇近七千多字的文章中是含蓄而又有力地渗透于每一处字里行间的。
一
“而今懒对菱花”,猜一个人名。这是妈妈给我们出的一个灯谜。谜底:曾照勤,我爸爸的名字。
谜语不是妈创作的。妈很爱看书,但她不像爸那样对文字游戏有浓厚的兴趣。她记得这个谜语,大概是因为它和照镜有关。妈常说,爸很紧张自己的仪容,很喜欢照镜,每次出街之前,一定要在镜子前花上半晌,把头髮梳得贴贴服服,一根也不能乱。妈曾笑?说,我弟弟像爸爸,对?镜子梳头很认真;我却像她,连梳子也懒用。
爸是那么注重仪容,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每对?镜子,一定难受极了。
二零零五年五月初,医生跟我和弟弟说,爸患了胆管癌,大概只能多活几个月。我们听了,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但也并不完全感到意外:我们都注意到,爸在过去几个月不断消瘦,整个样貌都变了。当医生叫他去做特别检查,我们便估计是凶多吉少了。
五月份那些日子,爸每次见到我们和他的孙女儿,都会带点惶恐地问:“你们还认得我吗?”因为镜子告诉他,他已不是我们熟悉的模样,而且每天在变,变得更加难看。他心里的痛苦,可能比病魔对他身体的折磨更难受。
爸没有像医生说,多活几个月。那折磨他的日子,只延续了两个多星期。五月二十日清晨,他就离开了我们。医生对这感到很诧异;朋友们却说,这是福气,是爸一生为人善良积来的福气。
二
曾门育才 严父之功
爸爸在一个大家庭里长大。我的祖父是独生子,祖母可了不起,生了八个儿子、六个女儿。我爸有五个哥哥、三个姊姊,在兄弟中排行第六,所以伯父和姑母们的子女都叫他六叔或者六舅父。我有两个伯父读上大学,我很相信我爸也是上大学的料子,可惜他运气不好,中学还没有毕业便遇上打仗,失去了升学的机会。
由于学歷不高,战后在香港找工作并不容易。他有一位很要好的中学同学,父亲是华商总会的重要人物,好像是秘书长或者什么的。凭他介绍,我爸在华商总会找到一份文员工作。华商总会后来改名为中华总商会(“中总”),爸在那里工作了超过半个世纪。
对于我小时家里的生活,以及当时爸爸的模样,现在已是印象十分模糊了。只记得家境并不好,我三岁前住过荷李活道的板间房,曾经睡?时给一个从床上的杂物架掉下来的喷水壶打中眼角,令我血流披面。后来二姑母、四伯父和我爸三家人,加上??和两个没有成家的伯父,合租了坚尼地城学士台六号二楼,一厅三房,还有冷巷,住了九个大人和十一个小孩,好不热闹。我们一家五口住一个大约一百平方呎的房间,条件比以前好得多了。我从幼稚园到大学二年级,一家人都住在那里。
有一段时间,爸要打两份工。每星期有几晚,在中总放工后,还要到另一个商会去做一份会计之类的兼职,晚上九点多钟才回到家,独个儿吃妈给他留的饭菜。大概由于生活和工作的压力,爸年轻时很暴躁。有时他和妈吵起架来,不但样子兇、声音大,而且家里的玻璃杯、暖水壶、镜子等,凡是可以打碎的,他都抓起来摔到地上,我和弟妹们只吓得缩作一团,在墙角里啜泣。
我五、六岁时有一晚,爸又是晚了回来,一个人在吃饭,我在地上拿?两架玩具车在玩撞车,一边撞,一边说了一句从伯父那里学来的、跟撞车动作配合的粗口。爸停了筷子,瞪?我喝骂。我歇了一会继续玩,那句粗口又禁不住脱口而出。爸不再警告,拿起他穿?的拖鞋,猛力向我扔过来。我记不得给打中哪里,也记不得有多痛,只记得吓呆了,以后再不敢在他面前说粗口了。
我和弟弟很爱到街上玩,跟其他孩子追逐、踢球。爸不喜欢我们在街上玩得太久,“玩得忘了形”。有时我们在街上玩,老远见到他回来,便马上跑回家,还要装出脸不红、气不喘,没有“玩得忘了形”的样子。有一次跑迟了,在家门外给爸着?,他随手执起靠在门边的一枝竹竿,使劲往我们身上打,我们兄弟俩一点也不敢吭声。
三
照料儿女 言传身教
爸发怒时很可怕,不发怒时很好玩。他有空在家里和我们一起的时候,会给我们讲故事、说笑话,又会和我们捉象棋、斗兽棋、波子棋,玩纸牌游戏、玩魔术,或者一起去破解报纸上的填字游戏和各种智力谜题。这些都是妈不会做的。
我们一家人也有不少快乐时光。有些傍晚,爸不用上夜班,晚饭后,我们一家人到薄扶林道散步。沿途都是香港大学的建筑:首先是利玛窦宿舍,接?是何东夫人纪念堂,然后有几座像是教学或实验楼,都是外国人名字命名的。那里的行人路很宽,楼房和行人路之间还有花槽。爸妈边散步边喁喁细语,我们三个孩子在他们周围追逐嬉戏,有时爬到拦?花槽的石壆上玩,已经很满足了。合季节时,清香的鸡蛋花掉满一地,我们还可以收集起来,带回家里连成一串,挂在窗子旁。
我们一家人都不习惯用言语或行动互相表达感情,谁都从来不会给谁抱一抱、亲一亲,或者讲句“我爱你”之类的话。有一次,爸爸和我坐在床上捉象棋,弟弟忽然走过来,丢下一张卡纸便跑开,弄得棋子都乱了。我们都一怔,爸气恼地把那卡纸扔到一边,重新摆好棋子。我拾起卡纸,看清了是什么,把它递到爸的眼前。原来那是弟弟专门给爸爸画的一张生日卡,画好了却不懂怎样交给爸。爸看了,脸色有点尴尬。我想爸心里不可能没有感受,只是不懂对弟弟怎么表示。
四
我自小就很羡慕爸写的一手好字。每逢过年,厨房里贴的“定福灶君”、“天官赐福”,家门前贴的“五方五土门神”、“前后地主财神”,都要更新;这时??便会拿红纸来叫爸写,我就在旁欣赏。那时小学还有“习字”课,要写大小楷毛笔字。爸每看到我的大小楷习作,脸上的表情就像在街上看到死老鼠般。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爸给我买了一本《黄自元间架结构九十二法》,要我照?学写字。学了一段时间,我写的字总算有点规矩,给他取笑也少了。
爸在商会(这是爸对中总的叫法)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抄写和印製文件。在没有电脑和打印机的年代,复印文件的方法是油印:把蜡纸放在有网纹的誊写钢版上,用钢尖誊写笔在上面书写,然后放到油印机印刷。爸经常要把写蜡纸的工作带回家里做。他在写,我就在旁边看。爸对他的这份工作不但十分认真,而且显然十分喜爱。我常觉得他不像在抄写文件,而是在製作艺术品。
除了抄写文件之外,爸也要做中文打字。那时的中文打字机,操作方法是将一颗颗铅製的字粒打在蜡纸上。打字的速度,决定于打字员需要用多少时间在一个长七十行、宽三十五列的字盘里找到他要的每一颗字粒。字粒怎样排列、打字员怎样记忆它们的位置,十分重要。爸说,排列时除了按字的部首和笔画之外,加上粤音九声,找字可以更快。我很小的时候,就从爸那里学会了辨别粤音九声,懂得怎样分平仄了。
我比弟妹有较多机会跟在爸的身旁。爸参加商会员工的旅行野餐等活动,都会带?我。他曾多次带我到他的办公室,让我看他怎样操作中文打字机和油印机。我还曾经跟他一起在商会会所里“打地铺”留宿:商会换届选举,爸要整晚留在会所里看管票箱,不能回家睡觉。不知为什么,他让我留在他身旁,那是我最早的“宿营”经验。
五
勤力顾家 望子成龙
爸整天在外面工作,妈整天在家里忙碌。他们的希望,都寄託在我们兄妹三人身上。爸妈省吃俭用,但和我们读书有关的开支,爸从不吝啬。爸妈对我们的学业要求很高,监督很严。每天晚上,爸妈不管多么疲倦,都要对?我们的学生手册,督促我们做完所有功课,并且把当天上课教的书全部读熟,才准上床睡觉。直至我们升上中学较高的年级,学习内容超出了他们能够监管的程度,同时他们也开始相信我们学习的自觉性,爸妈才放松对我们的监督,给我们高度自治。
我们三兄妹也没令爸妈失望。我和弟弟先后考进了圣保罗书院,妹妹入了庇理罗士女子中学,三人在学校里成绩都不错,有很好的机会升读大学,这正是爸妈的梦想。
由于我是老大,我想爸对我的期望是最高的。一九五八年小学会考(即后来的升中试),我侥幸考了个全港第一名。学校收到消息,通知了我爸,并且告诉他将在第二天早会上向全校宣布。早会是不让家长出席的;爸那天一早来到学校外面,隔?围墙听宣布。之后他到处对人说,家里出了个状元。
爸要送我一隻手表,作为奖励。以我们的家境,手表是很名贵的奢侈品,爸自己也从未戴过。那天傍晚,我做完功课,独个儿躺在床上发白日梦;天色已转暗,屋里还没有亮灯。爸放工回来,一走进房间便笑?说:“Watch!”然后从他腕上解下新买的手表,拿到我面前。我高兴得从床上跳起来,伸出手让爸给我戴上。我的手腕太小,表身太大,表带又太长,怎么也戴不牢。第二天爸拿去在表带上多钻几个孔,才勉强把新手表固定在我手腕上,回到学校被老师和同学们取笑了一番,不过我心里还是兴奋了很久。
我读中学的几年,爸大概从老师那里听到不少夸赞我学业成绩的话。到我快要参加中学会考的时候,爸到处对人说,该年的中学会考要出一个十优状元。这次我可丢了爸的脸:我只考得五科优,其他多科临场失了手,没有考出预期的成绩。我不知道爸有多失望,不过他没有对我责备、埋怨,只是轻轻地问了一句:成绩是不是没有预想的好?
步入中年,爸脾气好了,笑容多了,身体胖了。家庭环境比前好转了:爸大概升了职,薪金多了;我从中三开始替其他孩子补习,给家里增加点收入。房间虽然挤迫,爸仍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张新书桌。我读中六那年,爸更满足我的要求,分期付款购了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定价三千多元,等于爸几个月的薪金)。
一九六五年我考进了香港大学,爸妈梦想的第一步实现了。弟妹的学业发展也很顺利,跟在我的背后,不久也要进入大学。眼见艰难日子很快就可以抛在脑后,我们一家人正稳步迈向幸福的前景。
怎也想不到,一九六七年,天忽然塌下来,爸妈的梦想像爸摔在地上的镜子,一下子完全粉碎。

扫一扫,关注大公网《微香港》公众号
- 刘乃强:看看周边 想想香港2015-05-18
- 方靖之:“滚动民调”乏贊助钱何来?2015-05-18
- 黄友嘉冀热议强积金置业2015-05-18
- 关昭:深切悼念杨光会长2015-05-18
- 刘乃强:香港人固步自封将玩死自己2015-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