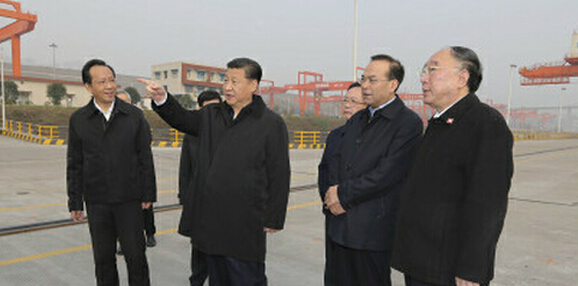董鼎山的书房/海 龙
编按:本园地“纽约客闲话”栏目作者董鼎山先生痛于去年十二月十九日离世,“大公园”同仁深感哀悼。本文作者海龙先生与董先生过从甚密,特撰此文以致哀思。
董鼎山先生是个广交朋友的人。但在美国,即使再好客的人交朋友也大多在公众场合会面。交情深了,喝咖啡、吃饭喝酒,大都在饭店或咖啡馆。敢说到过某人家就知道其交情一定不一般。鼎山公在纽约住了六十年,去过他家的朋友当然不少,但敢于吹牛进过老爷子书房的却不一定多。
因为,一般美国人家规矩是密友请入家,被邀到家的友人大多在主人居停处所如书房、客厅或者起居间相聚谈玩。即使是关系过硬者也不能东张西望阅书看画或者评议装潢古董等等。董先生是老美国,习俗上当然不例外。但他家有一处不同就是他宁可让客人入客厅、起居间甚或厨房(可以用餐),但鲜少让来客去那在老美认为更具公共性的书房。
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个小小的秘密。朋友间都知道董鼎山太太非常乾净优雅是个有洁癖的人。每有朋友来,她必?力清洁房间美化环境,即使在她即将辞世的高龄也是必须准备好鲜花、把房间整理得优雅美丽才接待客人。而且按照欧洲习惯﹙董鼎山太太是瑞典人﹚家里一定要准备好下午茶、点心和咖啡待客,几十年如一日。董夫人蓓琪女士对所有朋友都优雅高贵、亲和有礼。鼎山先生跟朋友谈话讨论她从不参与、打岔。前几年我跟鼎山公合作出书是他家常客,跟我熟悉了的老太太温婉招待,抽空会聊一聊。她总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示人,是一个备受尊重的女士。
董夫人的教养让她自尊且模范持家,家是她的领地,她必须把一切打理完美才愿意示人。但是,这个家庭有一个死角成了她的心病,那就是董先生的书房。
董先生写作日以继夜,平时搜罗材料铺天盖地。书房里自然是杂乱无章。书摞书纸缠纸桌上地上见缝插针,有时候老爷子几篇文章同时写,资料自然混乱夹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莫衷一是。其实,外人看到这样混乱如废品收购站的情形难免挠头,但对于董先生来讲这却井井有条。不管多么乱,他自己明白。要找的东西手到擒来,如鱼得水。可是,如果一旦有人替他整理打扫归类甚或稍微挪动了地方,老爷子就会一筹莫展沮丧发火。就这样,长年以来董先生养成了自己的书房不许打扫和整理的习惯。其实不止董先生,好多写作的朋友当能理解这种现象。
董太太当然知道挚爱老爷子的这个怪癖,但同样酷爱自己优雅主妇名声的她也有自己的坚持。于是他们约法三章,她可以容忍老爷子这种执拗,但是老爷子也必须回护她的脸面不准任何人去他的书房。所以,在回忆老爷子的文章中我们读到很多对他不准进他书房的神秘回忆等等。甚至他最知心的朋友和编辑们都不知道他书房的秘密。
其实,他的书房并没有秘密。我去过,而且不止一次。那是我跟董先生合作写书的时候。我当然知道他书房的忌讳,凡他取书和取材料时我都在客厅等他。有一天蓓琪出去有事,董先生在书房里大声叫我。我怕他需我帮助正在踌躇,董先生却打开书房门冲我调皮挤眼让我进去,神情中有一种顽皮闯了祸的喜悦在内。老爷子的书房不大也不算过于凌乱。当然桌上架子上地上摆满了书报,较狭窄的空间有电话传真机打字机电脑还有剪刀胶水之类比较拥塞。这里没有顶天立地的书架因为书都放在客厅书橱里了。他的书房更像是一个工作间。我自己写作时也是这样情形:乱,但属一种特殊有序的状态;不同的是一般我们写作有时间性,写完后大多恢復常态。而董先生几乎一生写作不停,因而他勉力奋斗跟太太争执出了一片天,因他永远都是在写作。这个书房因之有了永恆的意义。
有了这一次,我得到了特许。老爷子大概觉得豁出去了,也就有了其后的一而再再而三。我去他家而董太太不在时他经常邀我去书房帮他修电脑看存档,甚至请我跟他去?室查传真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在他过世前的傍晚嘱咐我去他书房桌上取他最后一篇作品暨他为我们给他编书写的序言的缘由。董先生过世前,念念不忘这篇东西,他的女儿不认识汉字,他怕女儿把这篇最后心血结晶的文字给扔了。我已经跟他女儿联繫好了不久会去他书房取。
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向他致敬,跟他告别。但,这次拜访书房应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情何以堪?也许,这就是董先生挤眼时的那冥冥中的缘分,让我踏入书房,替他这一生最后完成他写作的仪式。
- 物联网专利 全球企业居首2016-01-07
- “蓝剑”赠英雄 筑巢引金凤2016-01-07
- “陌生人”变最信赖伙伴2016-01-07
- 中兴通讯近年研发数据2016-01-07
- 中兴“智造”覆盖160国2016-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