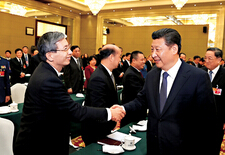曾钰成大公报刊文 怀念父亲曾照勤逝世十周年
八
照亮家庭 默默守护
弟弟的被捕,令熟悉我们一家的人(包括几乎所有住在学士台的街坊,因为我们在那里住了十七年)感到惊讶,有些人还对我们有点同情;妹妹接着被捕,却令所有人都相信我们一家是捣乱分子,对我们“另眼相看”。用妈以前的说法,他们都把我们当作患了麻风一样。爸要如常上班,我如常上课,留下妈一人,只能躲在房间里哭。不得已要到市场买菜,便要抵受四周敌意的目光和毫不掩饰的闲言闲语。
“把我们当作患了麻风”的,不仅是西环的街坊。我原来有几个补习学生,他们的家长都通知我不用继续了,其中包括爸的一个认识了多年、经常来往的好朋友。这位世伯本来对我也很好,他很清楚我的左倾思想,但仍很喜欢找我聊天。他的儿子读书很不错,要准备升学,所以决定找我替他补习。刚说好什么时候开始,我家就出事了。世伯通知我爸,补习暂不用了。连最好的朋友也掉头而去,爸告诉我时,难掩伤感、失落。
老朋友、旧相识忽成陌路,新朋友却纷至沓来。弟妹先后被捕之后,很多我们原来不认识的左派人士来找我们,给爸妈和我送来慰问、关怀和鼓励。他们见我妈独留家中容易发愁,便介绍她到中业中学小学部当教师。妈虽是当了二十多年家庭主妇,但她的文化水平本来不错,从监督我们兄妹读书中,大概也积累了一点教学经验,到学校工作,还算胜任愉快。
爸决定搬家,从我们熟悉的西环迁到北角,避开旧街坊,来到新环境,开始新生活。弟弟出狱后获《大公报》聘用,妹妹投身爱国文化事业,后转到《文汇报》任记者,我离开大学后到了培侨中学当教师。于是一家五口都任职爱国机构,成为不折不扣的红色家庭。
这不是我们小时候爸爸的愿望,但他从没有埋怨我们令他失望,没有拿我们和一些凭学业成绩出人头地的成功人士来攀比。一家人活得开心,爸似乎就心满意足。每当他听到学校或报馆称赞我们三兄妹的工作表现时,他就像以往拿到我们的考试成绩表时那样高兴。
如果不是香港回归,我和弟妹很可能和爸一样,各自在爱国机构的岗位上工作至退休,过着并不富裕但也安稳的生活。
九
经历过政治风暴给我们一家带来的冲击,爸晚年的心愿,应是希望我们脱离尘网,像我们很多同辈一样平静地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让他不用再担心突然有灾祸降临在我们头上。然而,命运却不肯让他释怀,要他活到最后一刻仍为我们担忧。
正如我到培侨中学工作事前并没有和爸商量,我组织政治团体、参加议会选举,也是做了之后他才知道。一九九二年,培侨中学刚成为直接资助学校,教师工资终于可以跟津贴学校看齐;我作为校长,收入足以维持相当舒适惬意的生活。我偏不安于份,去当了民建联的主席,成为经常见报的争议人物。爸这时大概也料到,我在学校里做校长那份工作,不可能做到退休了。他或会替我担心,但他没对我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留意我做的一切。
爸是我最忠实的“粉丝”。我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接受的每一次采访,出席的每一个电台或电视节目,以及传媒有关我的每一段报道,他都不会错过。他十分在意人们对我的评论,听到对我肯定的评价,他会满心欢喜;遇有负面的批评,不管批评者是谁,有理没理,爸一定为我不服气。他很少跟批评者理论,却会满脸不屑地给我覆述某某人的话,为我抱不平。我获得的每一项成就,遇到的每一宗挫折,爸的感受可能比我更强烈。我的地区办事处开幕,不经意跟他说了,他一早便兴高采烈地来到参观。我输了选举、我因民建联选举失利而鞠躬下台,他比我更加失望难过。爸不在之后,我才愈来愈感到内疚;爸对我的表现,对我成败得失的感受,我一直麻木不仁,没有给放在心上。
记不清从哪时开始,爸和我养成了每天早上一起饮茶的习惯。我们不同住;我很早起床,爸比我更早,我们上班前便在茶楼相聚。我们很少谈话;我对着爸静坐那半个小时,就有“宠辱皆忘,其喜洋洋”的感觉;而爸看着我悠闲地喝茶、吃点心,似乎也很满足。每天结帐都是由爸付钞,我从不会和他争。我对朋友说,很惭愧,几十岁了,饮茶还要爸结帐。朋友说,不用介意,你肯陪爸饮茶,他已很高兴。听他这样说,我更感歉疚。
十
勤劳一生 为家牵情
大约二零零零年左右,妈开始有脑退化症的徵兆。起初,当我们看到妈记错事、认错人、说错话、反应迟钝时,都不大以为意,还拿她的失常表现来取笑。后来情况渐见严重,爸告诉我们妈在家里做出的一些危险行为(例如有一次她煮饭时把电饭煲放到火炉上烧),我们才开始担心。爸独力承担照顾妈的责任。家里只有他们俩,没请佣人;爸从不会对我们说他应付不来,我们既没有充分了解爸的困难,也就未有认真研究可以协助做些什么。我们从理论上明白,脑退化症病人自己未必感到难受,照顾她的亲人是最难受;但我们没有因此对爸给予关怀和支持,有时见他对妈发脾气,更怪责他不够耐性。直至爸走了,我们自己和妈相处,才惊觉爸先前所受的痛苦。爸知道自己患了重病,很可能要比妈早离世时,最令他恐惧的,不是死亡,而是他走后妈怎活下去。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九日下午,我正在深水埗一个屋邨出席居民活动的时候,收到爸打来的电话,说他很辛苦,想到医院去。我把主持活动的工作交给伙伴,驾车到爸的家,把他送进医院。当晚,我和弟弟见到爸样子很辛苦,便守在他的床边,不敢离开。过了晚上十一时,爸坚持要我们回家睡觉,说:“你们留在这里也没用。”我们见医生说他暂时没有危险,便各自回家了。翌日清晨,医院的电话来了。我们赶到医院,爸已在昏迷状态。护士告诉我,爸刚才还在喊着我的名字,但我们已再听不到他说话了。
办完了所有手续,医院通知我去领爸的遗体。学校里一位职员陪我去,她看见爸的遗容,即冲口而出:“他还有话要说。”
是的,爸还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事情放不下。放不下妈妈,怕她没人照顾,在家里出事。放不下我和弟弟,怕我们做的事人们不喜欢,我们要捱骂捱批。放不下妹妹,放不下孙女儿。还有放不下那许多他藏在心里没有跟我们说的事。他牵挂的太多,来不及一一嘱咐我们,便匆匆走了。
爸在时,我经常在梦中见到他。他走后,这十年里我竟然一次也没有再在梦里和他相见。这也许倒好,要是见了,恐怕我仍是不懂对他说些什么,可以表达我对他的感情。

扫一扫,关注大公网《微香港》公众号
- 激进派为阻政改搞事不断 十大专生冲击典礼挑衅林郑2015-05-19
- 饶戈平:民意基础胜“公提” 无提委会无普选2015-05-19
- 林武:政改合宪合法 为现阶段最合理方案2015-05-19
- 龚如心遗产归属揭晓 华懋基金仅为受托人2015-05-19
- 谭志源:尽最大努力推动政改2015-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