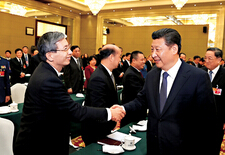曾钰成大公报刊文 怀念父亲曾照勤逝世十周年
四
我自小就很羡慕爸写的一手好字。每逢过年,厨房里贴的“定福灶君”、“天官赐福”,家门前贴的“五方五土门神”、“前后地主财神”,都要更新;这时嫲嫲便会拿红纸来叫爸写,我就在旁欣赏。那时小学还有“习字”课,要写大小楷毛笔字。爸每看到我的大小楷习作,脸上的表情就像在街上看到死老鼠般。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爸给我买了一本《黄自元间架结构九十二法》,要我照着学写字。学了一段时间,我写的字总算有点规矩,给他取笑也少了。
爸在商会(这是爸对中总的叫法)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抄写和印製文件。在没有电脑和打印机的年代,复印文件的方法是油印:把蜡纸放在有网纹的誊写钢版上,用钢尖誊写笔在上面书写,然后放到油印机印刷。爸经常要把写蜡纸的工作带回家里做。他在写,我就在旁边看。爸对他的这份工作不但十分认真,而且显然十分喜爱。我常觉得他不像在抄写文件,而是在制作艺术品。
除了抄写文件之外,爸也要做中文打字。那时的中文打字机,操作方法是将一颗颗铅製的字粒打在蜡纸上。打字的速度,决定于打字员需要用多少时间在一个长七十行、宽三十五列的字盘里找到他要的每一颗字粒。字粒怎样排列、打字员怎样记忆它们的位置,十分重要。爸说,排列时除了按字的部首和笔画之外,加上粤音九声,找字可以更快。我很小的时候,就从爸那里学会了辨别粤音九声,懂得怎样分平仄了。
我比弟妹有较多机会跟在爸的身旁。爸参加商会员工的旅行野餐等活动,都会带着我。他曾多次带我到他的办公室,让我看他怎样操作中文打字机和油印机。我还曾经跟他一起在商会会所里“打地铺”留宿:商会换届选举,爸要整晚留在会所里看管票箱,不能回家睡觉。不知为什么,他让我留在他身旁,那是我最早的“宿营”经验。
五
勤力顾家 望子成龙
爸整天在外面工作,妈整天在家里忙碌。他们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兄妹三人身上。爸妈省吃俭用,但和我们读书有关的开支,爸从不吝啬。爸妈对我们的学业要求很高,监督很严。每天晚上,爸妈不管多么疲倦,都要对着我们的学生手册,督促我们做完所有功课,并且把当天上课教的书全部读熟,才准上床睡觉。直至我们升上中学较高的年级,学习内容超出了他们能够监管的程度,同时他们也开始相信我们学习的自觉性,爸妈才放松对我们的监督,给我们高度自治。
我们三兄妹也没令爸妈失望。我和弟弟先后考进了圣保罗书院,妹妹入了庇理罗士女子中学,三人在学校里成绩都不错,有很好的机会升读大学,这正是爸妈的梦想。
由于我是老大,我想爸对我的期望是最高的。一九五八年小学会考(即后来的升中试),我侥幸考了个全港第一名。学校收到消息,通知了我爸,并且告诉他将在第二天早会上向全校宣布。早会是不让家长出席的;爸那天一早来到学校外面,隔着围墙听宣布。之后他到处对人说,家里出了个状元。
爸要送我一只手表,作为奖励。以我们的家境,手表是很名贵的奢侈品,爸自己也从未戴过。那天傍晚,我做完功课,独个儿躺在床上发白日梦;天色已转暗,屋里还没有亮灯。爸放工回来,一走进房间便笑着说:“Watch!”然后从他腕上解下新买的手表,拿到我面前。我高兴得从床上跳起来,伸出手让爸给我戴上。我的手腕太小,表身太大,表带又太长,怎么也戴不牢。第二天爸拿去在表带上多钻几个孔,才勉强把新手表固定在我手腕上,回到学校被老师和同学们取笑了一番,不过我心里还是兴奋了很久。
我读中学的几年,爸大概从老师那里听到不少夸赞我学业成绩的话。到我快要参加中学会考的时候,爸到处对人说,该年的中学会考要出一个十优状元。这次我可丢了爸的脸:我只考得五科优,其他多科临场失了手,没有考出预期的成绩。我不知道爸有多失望,不过他没有对我责备、埋怨,只是轻轻地问了一句:成绩是不是没有预想的好?
步入中年,爸脾气好了,笑容多了,身体胖了。家庭环境比前好转了:爸大概升了职,薪金多了;我从中三开始替其他孩子补习,给家里增加点收入。房间虽然挤迫,爸仍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张新书桌。我读中六那年,爸更满足我的要求,分期付款购了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定价三千多元,等于爸几个月的薪金)。
一九六五年我考进了香港大学,爸妈梦想的第一步实现了。弟妹的学业发展也很顺利,跟在我的背后,不久也要进入大学。眼见艰难日子很快就可以抛在脑后,我们一家人正稳步迈向幸福的前景。
怎也想不到,一九六七年,天忽然塌下来,爸妈的梦想像爸摔在地上的镜子,一下子完全粉碎。
图:曾照勤夫妇二零零五年最后一次旅游,摄于肇庆
六
我不知道爸妈是怎样收到弟弟在学校里被捕的消息,也记不清是谁通知我。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学校在暑假后刚开课不到一个月。我只记得那天傍晚我回到家里时,爸妈都不在家。我一进门便见到四伯父在厅子里对着我的妹妹训话,妹妹在不停地哭。我立即叫妹妹返回我们的房间,把房门关上。
爸在中总这家“左派机构”工作。作为中总的僱员,他在家里长期订了一份《文汇报》,并且不时有《人民画报》一类的刊物带回家。此外,每有来自内地的电影或文艺表演,爸都会拿到入场券,让我们去看。这些“左派宣传”对我们兄妹有多大影响,很难准确评估。不过我们绝不是只接受左派宣传的“洗脑”;要说“洗脑”,我们每天看到和听到的,大部分倒是反共的东西:家里的长辈,除了我们爸妈之外,都不会为共产党说半句好话;我们在学校里的老师,多数是反共的,其中有的几乎每天都在学生面前骂共产党;我们家里不只有一份《文汇报》,同时也有反共报纸。
爸很少和我们谈政治。他和妈都和上一代很多人一样,害怕政治。他们最关心的,是我们要用功读书,不要学坏。我们三兄妹的“左派思想”,其实都是分别从外面得来的,或者可说是时代的产物。爸知道我和一些“左派人士”交朋友,思想愈来愈“左倾”,可能有点担心,但他从没阻挠或者反对。我想他和我一样,觉得那些“左派人士”都很正派,我跟着他们不会学坏。
一九六七年,由工潮演变成香港整个左派阵营参与的“反英抗暴斗争”,愈来愈激烈。到五月,大规模的反英示威游行几乎天天发生,并经常导致暴力冲突。防暴警察多次向示威人群放催泪弹,很多人被打和被捕。有一天,我在中环遇上示威游行,我走到游行队里,跟着其他人一起喊口号。那天晚上,爸回家时神色凝重地把我拉到房间里,拿出一份英文晚报给我看。报纸的头版刊登了一张很大的当天示威的照片,清楚地看到我在其中。
爸担忧地问:“你知道给记者拍了照片吗?”他从来没想到我会参加街上的示威行动。“反英抗暴斗争”将怎样发展,我们不知道,但爸肯定不希望我们做出任何会影响我们个人前途的事。我已忘了那天晚上我怎样对爸说,大概是承诺我会尽量小心吧。
想不到最先出事的是弟弟。
七
曾子被捕 挺身而出
在家里,弟弟从来比我乖。我生性好辩,跟长辈驳起嘴来经常不知分寸,被斥不懂礼貌。我个子矮小,但和其他孩子打起架来却可以很凶,令他们的家长很不高兴。我自十多岁开始便和几个伯父合不来,跟四伯父的关系尤其恶劣。弟弟没有这些问题。他很少跟人吵嘴,更不会动手打架。从家里到学校,弟弟的人缘比我好得多。我们开始关心政治之后,弟弟的表现十分平静,很少像我一样跟意见不合的人争论得脸红耳赤。总的来说,弟弟为人平和忍让,从不会因情绪冲动而做出鲁莽的事。所以,弟弟被拘捕,爸妈和很多认识我们的人都十分意外。他犯了什么事呢?在学校里,在上学的时间(不是擅闯校园)、下课的时候(不是违规旷课),向同学们派发传单(不涉暴力欺诈)。因这样的行为被拘捕判刑,在今天看来是匪夷所思,不管传单上是什么内容。但当时香港是在非常状态,校长一见有人派单张便报警,警察一到便拉人,拉了人便检控。法庭审理弟弟的案件时,爸要上庭作证。他面对很困难的选择:为弟弟认错求情,争取轻判,还是支持弟弟的作为,在庭上谴责港英当局,不管弟弟可能被重判,多受牢狱之苦?
爸大概挣扎了很久。结果,他在法官面前战战兢兢的只说了一句话:“我儿子做的事是对的。”这句话,惹来法官一顿痛斥,弟弟被重判两年刑期,还要被某些报纸讥讽辱骂一番。但这句话,在我们一家人里成为新的凝聚力,让弟弟挺起胸膛面对牢狱的磨练。
弟弟被捕后不到一个半月,妹妹遭到同样的命运:在学校里和其他十三个同学一起被警察拘捕。她们为了一个被校方停课的同学,集体与校方理论,被校方召警拉人,我妹妹被判囚一个月。

扫一扫,关注大公网《微香港》公众号
- 激进派为阻政改搞事不断 十大专生冲击典礼挑衅林郑2015-05-19
- 饶戈平:民意基础胜“公提” 无提委会无普选2015-05-19
- 林武:政改合宪合法 为现阶段最合理方案2015-05-19
- 龚如心遗产归属揭晓 华懋基金仅为受托人2015-05-19
- 谭志源:尽最大努力推动政改2015-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