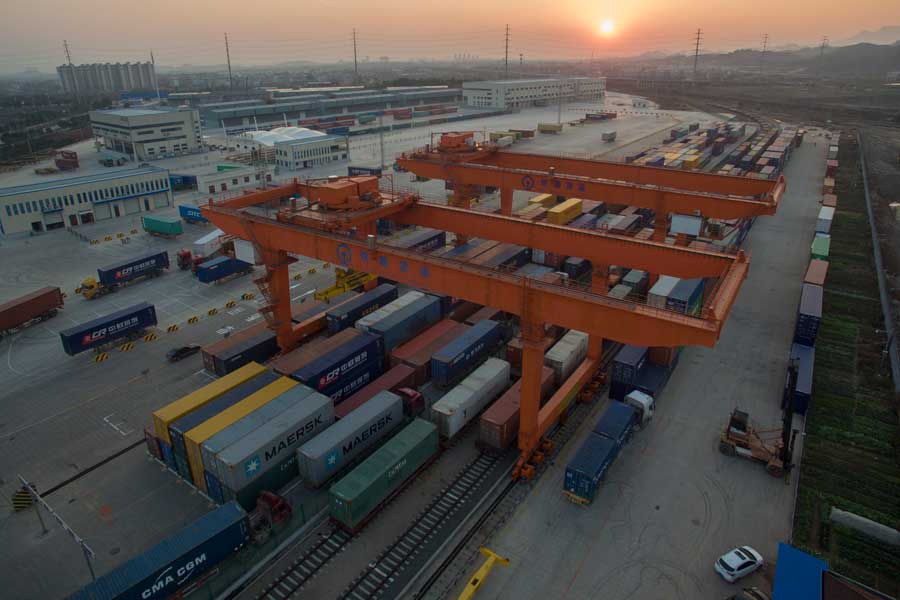从外婆家带回的年礼

文|卞长生
在我还没上学时,每年正月初二,父亲总是要带着我去外婆家走亲戚。到外婆家,要步行八华里崎岖不平的土地,就繁荣程度说,外婆家所在的村,是一个农舍零落、偏僻寂寥、只有几百口人的小村庄,相比我们所处人口稠密、熙熙攘攘的集镇,没什么可吸引我的,唯有从外婆家带回来的年礼黏饽饽,吃在嘴里,齿颊生香,像磁石一样,诱惑着我。
去外婆的路上,因穿的是新缝制、硬邦邦的布鞋,两只脚感到很受挤压,走一会儿,就耍赖,蹲下身来,对父亲说:我不走了,我走不动了。父亲开始很生气,可一会儿,就转阴为晴,哄我说:你不是最爱吃外婆家的黏饽饽吗?外婆捎信说,已经早就给准备好了,坚持一下,我们得把黏饽饽拿来啊。没骗我吧。我说。父亲点点头。我顿时有了精神,用手把硬邦邦的鞋帮抻一抻,跺跺脚,继续走路。
黏饽饽,是用黏高粱米制作而成,我们家里没有黏米,唯有外婆家才有,那是因为,在我们的集镇不种植黏高粱。和父亲下地的时候,偶然一次,看见沟边有一两棵长相不同寻常的高粱,问父亲,他说那是黏高粱。高高的秸秆,脖颈仰得和地面几乎呈九十度角时,才能看到它的穗子,那浮游在顶端的码子,像散开的稀疏的颗颗小星,一个穗子上,结不了多少高粱颗粒,因产量不高,也就显得弥足珍贵。在我们人多地少的集镇,只有在沟边垫埂僻静处,零零星星见到它的身影,在那个以解决温饱为主、提倡粮食高产的年代,相对于多穗高粱,码稀低产的黏高粱,是不受待见的,只有像外婆家、居地多人稀的小村庄,在人们不大注意的地方,才有小片种植。外婆家占地利之先,产出黏高粱米,也就有了制作黏饽饽的条件。在外婆家吃午饭时,餐桌上,并没见到黏饽饽。我就对父亲耳语说,看来,今年是没黏饽饽了,父亲捅捅我,意思是,瞎说什么,外婆留着呢,作为年礼,给我们带着,你不要说话好了。我不听父亲的暗示,偏把说话的音量放得很大,说:我要吃黏饽饽,我要吃黏饽饽!此时,外婆说:别闹了,一会儿给你们去取。吃完午饭,外婆说:太阳还这样高,回家不着急。我高喊,我要回家。说是要回家,实际上,心里在敲鼓,怕外婆的主意变了,黏饽饽还未到手,我怎么能继续呆得住呢?
外婆家正房三间,堂屋的南面和北面的两道板门敞开着,地势很高,房前和屋后都有十几级石阶,回家要走南面的石阶,外婆要我们在堂屋等着,她下了北面台阶去偏屋取东西。是不是去取黏饽饽啊,我等不及了,脱开父亲的手,朝北面台阶走去,外婆回头看见我,喊:别跌着。就往回返,我执拗地一步两阶地朝外婆的方向走去,我小小的步幅,哪有意想的那样大的容量,一个跟头,就跌倒在石阶上。看着外婆挎着篮子走了过来,我从石阶上赶紧爬起来,朝堂屋的方向走去。那是冻硬了的黏饽饽,尽管如此,也闻到一股幽香,我伸手从篮子里拿出来一个,咬了一口,顿时,感到牙根冰凉,可香味却从唇齿间飘逸出来。到了家,把黏饽饽放在粥锅里,在沸水熬粥的同时,开始给冻僵了的黏饽饽解冻。此时,黏饽饽的形象,已经完全看不出原有端端正正、底部敦实、顶端尖细的样子,化身为黏稠的条状物。怎么才能把它弄到碗中成个一道难题。办法还是有的。把白瓷碗的边沿放在锅沿下面,用筷子把在粥锅里的黏饽饽夹住,慢慢地顺着锅底往边沿上拉。我在旁边早就等不及了,等黏饽饽下肚,照照镜子,嘴边成了花猫,留下一圈残留在皮肤上的黏饽饽的残渣,不尽感叹:黏,黏,真黏。把美味黏在嘴上,热在心头,外婆对晚辈的爱抚,也流淌出来,更预示着新的一年生活的甜蜜美好。
据说,在老家的乡间,一度曾流行以黏饽饽作年礼,是有寓意的,一是“黏”与年谐音,人们在这样欢乐的节日,吃上这样的美食,增加节日气氛。二是,黏饽饽的品性黏稠,有黏连、连接的意思,通过这样的年礼,把亲人之间的感情,像搅不开、黏稠的黏饽饽一样,紧密地连接起来。现在想来,这只是一种说法,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那时人们生活水准比较低,让人们送贵重物品,也承受不起,经济上不允许,只能从农家饭食中优中选优了。但是,尽管条件艰苦,庄户人家对年的文化,还是比较在乎的,也为了在新年图个吉利,于是,就给黏饽饽这贫民食品,戴上了璀璨的光环。

扫一扫,关注大公网《晨读香江》公众号
- 春联里的人文情韵2017-01-30
- 忆吾师汪经昌——学术严谨言谈风趣2017-01-29
- 日APA酒店谎话连篇2017-01-29
- 敦煌菜穿越千年 走入百姓年夜饭2017-01-26
- 兰州首家新概念影城开业运营2017-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