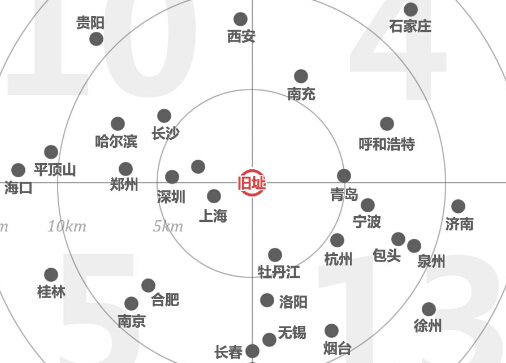于睿寅:历史的疮疤,你敢揭吗?

图:伊斯坦布尔 网上图片
文|于睿寅
近来“土耳其”成为热词。该国一些关于中国穆斯林的不实报道,让原本众多游客心向往之的异域国度,瞬间转为口诛笔伐的对象。此处并非要谈政治,因为任何新闻报道都难免存在倾向性,而在未透彻了解的前提下做到客观公正,难度极大。
这里要谈的一段历史,及一位作家。对他国国情认知存在偏差的土耳其人,即便对于本国历史所知的也是“部分真理”(half-truth)。今年恰逢亚美尼亚大屠杀一百周年的纪念,不可能指望在世的土耳其人(尤其是年轻一辈)对于自己先辈一个世纪之前的灭族行径坦然面对。因为这段黑历史鲜被提及,而为真相登高而呼的本国人,结局参照帕穆克(Orhan Pamuk)。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见容于母国政府、舆论的先例,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到高行健皆是,而二○○六年的得主帕穆克恐怕是最新的一位。帕穆克因言获罪是在二○○五年,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上一个整十年纪念,只因在接受采访时的一句“三万库尔德人和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害”。公开谈论此事是触犯土耳其法律的,而帕穆克为这句话既赔了钱,又遭了罪。作品被焚烧,生命遭威胁,充分体会了他惺惺相惜的印裔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当年的“礼遇”。这一切都被帕穆克记述在随笔集《别样的色彩》(Oteki Renkler)中。
未立法免牢狱之灾
但帕穆克并非心甘情愿地给自己贴上“言论自由斗士”的标签。他在二○○二年的小说《雪》(Kar)中就描绘了一位因为政治立场而不得不远离故土的主人公,带着极度痛苦的色彩。对伊斯坦布尔充满感情的帕穆克不想遭此命运,所以在说那句话时未用“种族屠杀”等敏感的词汇,甚至连杀戮者是谁都刻意模糊。无奈的是对于此事的敏感非但流淌在多数土耳其人的血液中,甚至写成了法律条文。这一“侮辱土耳其国格”的三百零一条款在帕穆克“口不择言”后几个月颁布,多亏“新法办旧罪”未被司法系统采纳,否则帕穆克怕有牢狱之灾。
十年过去,大屠杀居然已是一个世纪前的旧事了,但帕穆克依然如故。十年前联名声援他的作家,如厄普代克(John Updike)、马尔克斯(Garcia Marquez)和格拉斯(Gunter Grass)先后作古,而格拉斯三个月前的逝世更是让人再度感叹:我们需要敢于揭历史(尤其是本国历史)疮疤的作家。格拉斯早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在后期的作品中毫不避讳,且深刻反省自己的那段黑历史,也获得了多数读者的宽恕。更早之前《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惨遭枪袭,以及又被提及的一九八九年“拉什迪事件”,又让人看到某些群体对于指责其“缺乏宽容”的人赶尽杀绝的同时,恰是用自己的愚昧和愤怒证实了那些指摘。
成为真正土耳其作家
这也是过去十年里,土耳其让帕穆克惶惑的地方,幸而他看到了改变。二○一○年,伊斯坦布尔几所大学就此主题开办了研讨会,欢迎一切与“政治正确”相反的立场。这是进步。在上月结束的上海电影节上,讲述那段历史的电影《切口》(The Cut)公映,更是证明一国对于任何历史的蒙蔽,不可能逃脱全世界的眼睛。片中来自亚美尼亚的父亲侥幸逃脱土耳其人制造的劫难,却在回归故土后发现妻女走散,于是远渡重洋,终于在美国与女儿重逢。片尾镜头扫到埋葬?亡妻的墓碑,恰证明一百年前的历史纵然埋葬,却不可忘却。
故而,帕穆克觉得经历的这十年劫难,让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真正属于一国的作家,理应是不怕揭历史的疮疤。

扫一扫,关注大公网公众号
- 媒体:缅甸重判153中国公民背后的企图2015-07-23
- “呼罗珊”头目遭美空袭亡 提前知晓9.11恐袭2015-07-23
- 唐奇芳:改善中日关系 “治标”更要“治本”2015-07-23
- 安倍纸模释安保法愚民 网民轰儿戏幼稚2015-07-23
- 中国150名伐木工在缅遭判刑2015-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