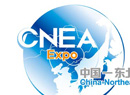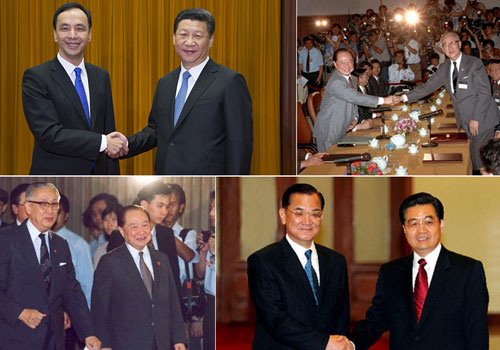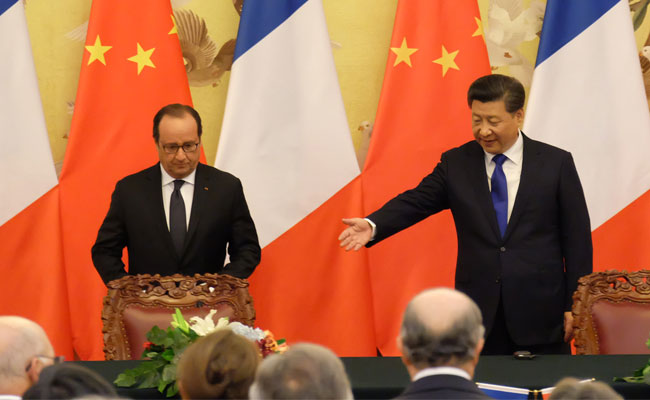小人物之歌\李梦

图:贾樟柯电影《小武》剧照\(作者供图)
上周末,国际文学节二○一五在港举行,我去中环听中国作家徐则臣的讲座,关于他十年前的一部中篇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
小说讲的是一群“漂”在北京的外地人的故事。这群人不论年龄、样貌或性格如何迥异,统统被冠以“底层人”的称呼。的确,在俗世的目光中,这些年轻男女的生活确实与“成功”二字相去甚远:无房无车无户口,连一份体面的工作也找不到,终日游荡在街头,靠办假证和贩卖盗版碟为生。然而,作者并未遵循功利主义或金钱至上的逻辑,将这些“底层人”写成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也不想用“无力”、“惶惑”或“绝望”来形容他们;相反,这些男女在徐则臣笔下,都是热烈饱满的,举止言行间都鼓胀?蓬勃的生命力。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敦煌以贩卖盗版碟为生,却在“下班”后回到出租屋里,观看《单车窃贼》(Ladri di biciclette)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夏小容在男友旷山因贩碟惹了官司之后,不哭闹不嫌弃,尽心尽力支撑这个三口小家度过艰难时日;保定因为办假证被关进拘留所,仍不忘嘱託敦煌照顾自己的女朋友七宝。如是种种,在徐则臣看来,都是所谓的“底层人”身上朴素却闪光的言行及情感。作者在《跑步穿过中关村》中,一直尝试将个体与其阶层属性剥离,以活生生的、饱满的笔触描述普通人以及介乎“可控”与“失控”间的平凡生活。换言之,办假证的七宝,以及贩卖盗版碟的敦煌,有喜恶有爱慾,有懦弱也经歷过正义感爆棚的瞬间,与你我无甚分别。
这样的笔调不禁让我想起导演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我一直是贾樟柯的影迷,虽然自从《语路》和《海上传奇》之后,对其影片的好感略有下降。虽说近年来的贾氏电影有“重复”之嫌,他本人也不时面对“自揭伤疤讨好外国人”等等指责,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位山西籍导演是目前中国为数不多的有情怀也有担当的艺术家之一,而这所谓的“情怀”,正体现在他对小人物的描摹上。
在贾樟柯早期的代表作中,主人公全部是小人物,有《小武》中小武那样靠偷窃为生的街边混混,有《站台》中坐在敞篷大卡车上四处搭台演出的县级文工团歌手,也有失业矿工、野模特以及人到中年面临婚姻危机的护士,等等。同样的,导演并未以俯视的角度拍摄他们,也不想将其片中人物标籤化或脸谱化,他只是“平视”,用长镜头、淡化情节的叙事和不动声色的情绪铺排,讲述片中男女的离别爱恨,绵密的感情以及欲言又止的心事。经得住无聊以及睏意磨折的观众往往在看过贾樟柯的影片后,从那些贴?地面的叙事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与片中主人公相似,我们又何尝不是在日復一日的倦怠和无聊中过生活,在望不见尽头的路上兜兜转转,游走在“找寻”及“失落”的两极。
其实,徐则臣的小说中,以及贾樟柯的电影里,角色的职业和居住地不过是个“外壳”,是作家和导演藉以搭建故事的道具或平台。不论漂泊在北京中关村、艰难打拼的外地人,抑或游荡在山西汾阳街头、无所事事的待业青年,他们面对的人生处境每每有?惊人的相似处。拨开“外壳”,扯去社会性和意识形态的禁锢,袒露在你我面前的,竟是一个大写的“人”字。书中和电影中人物经歷的惶惑失落也好,喜悦幸福也罢,在巴黎,在伦敦,在遥远的北方或南方的某座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同样也在经歷。
生活在俗世中的我们,时常被浮华的表象遮蔽,以为拥有了金钱、权力和地位,就能为自己挣得一点与这世界讨价还价的可能。说白了,日进斗金也好,衣不蔽体也罢,你我都是浩淼宇宙中的一粒沙,谁也不比谁更伟大更出色更成功,谁也逃不开生老病死和爱恨别离的轮迴。与宏阔时空相对照,任谁都是小人物,都无一例外地守?自己那可怜的一点爱慾过日子。而只有当一部小说或影片,像带刺的触角一般,穿过华美的衣和粉饰的墙,直戳到光明背后的暗面,明艷背后的凡庸甚至丑陋,我们才能说,这些文字和影像真正具备了某种打动人心的、素朴的力量。
- 北京观察:“十三五”重塑速度与底线\马浩亮2015-11-05
- 外媒关注“十三五”新商机2015-11-05
- 放开二胎年出生人口最多二千万2015-11-05
- 直面“中等收入陷阱”挑战2015-11-05
- 李克强:用新理念统领“十三五”规划2015-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