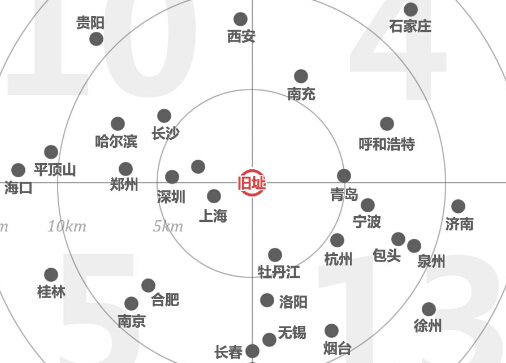鲁迅家的佣人不受气/霍无非
众所周知,鲁迅自小生活在一个封建没落的大家庭,从他幼年到离世,家中都离不了佣人帮工,就算是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分家另过,大家变为小家,与母亲鲁瑞及元配朱安在北京一起生活的三年,以及后来他与许广平在上海共筑爱巢,生下儿子周海婴,佣人始终是他家不可或缺的一员。
早年,鲁迅家的佣人是绍兴乡下的农村妇女,一九一九年冬举家迁到北京后,家中的佣人几乎还是来自江浙一带,这样从地缘上就有亲近感,她们吃得苦,粗活累活做得来,里里外外一把手,大体能与僱主一家相安共处。鲁迅像他的母亲那样,自小对家中的佣人是亲密无间的,没有颐指气使的呵斥和歧视,他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在他数个“长妈妈”中,尤对矮胖的“阿长”感情最深,这在他的回忆性散文《阿长和山海经》中有所描述。虽然胖“阿长”爱饶舌,四肢张开的睡姿挤得他吃了苦头,但她常给他讲些乡俗的宜忌,蕴含朴素的道理,不啻于启蒙教育。特别是她关心少年鲁迅的求知兴趣,出乎意料地购回了他朝思暮想的书籍《山海经》,真让他欣喜不已,冰释了对她除灭宠物鼠的前嫌,“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并深情地发出心声:“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长妈妈”们善良、勤劳的本性感染了鲁迅,成年后他也同情和善待家中佣人、人力车夫、烈士遗属等底层劳动人民。
当然,鲁迅一家善待佣人,和睦相处,并不是说佣人可以和主人平起平坐,两者是有别的。她们做事要听当家主人的吩咐,在北京八道湾大家庭时期,鲁家当家的是二弟媳羽太信子,僱请了管家、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採购等多名佣人,挥霍铺张,花钱无度,以致为兄的鲁迅看不下眼,出言相劝,招来怨恨,这应是与周作人反目并终生不再来往的主要原因。此外,佣人吃住也是要和主人家分开的。鲁迅搬离八道湾后,家中有两位佣人──王妈和胡妈,前者专门服侍鲁迅母亲,后者干杂活。鲁家有个规矩:佣人吃白饭不吃菜。因为菜是朱安烧的,佣人怎能食之,主人每天各给她们四个铜板买菜吃,这样看似苛刻,又在情理之中,生活上的事,鲁迅尽量顺茈擦芊A由茼隋w,是他不能完全左右的。
一九二九年九月,鲁迅在上海当了父亲,家务事骤多,僱请了同乡农妇王阿花,王阿花年轻漂亮,爱妆扮,喜串门,带孩儿的经验和责任心都欠些,竟让幼小的海婴受寒落下哮喘的病根,老来得子的鲁迅却没责怪她。王阿花是怕被有病暴虐的丈夫卖掉而离家的,丈夫得知她逃到鲁迅家,派人来追踪,准备把她劫回卖掉,鲁迅背负“强佔女人”的恶名,毫不胆怯,挺身而出,把这一干人挡在门外。与专此而来的乡绅谈判时,严正指出卖人是现在不允许的,最终,他仗义地掏一百五十元心血钱,帮王阿花赎了身,恢復了自由,甘当“冤大头”,让她获得新生。以后,鲁迅家又僱请了许妈,许妈不仅体壮能干,心肠也好,当小海婴患痢疾需禁食时,她看不得孩子捱饿,用私房钱悄悄买来饼乾,藏在别人家,偷茧驯L吃几块。她带小海婴到野外玩耍,捉螳螂,有时玩饿了,她就掏一两个铜板买点“老虎脚爪”、“麻油?子”等扬州提篮点心给他充飢……直到鲁迅病逝后,她才离开上海返回南通乡下。十年后,念旧的许妈满头银丝,步履蹒跚专程来上海看望许广平母子,见周海婴已长成一位帅气的初三学生,百感交集,心才释然。试想,如果鲁迅夫妇当年待她不好,是没有这份感情长途跋涉故人重见的。
鲁迅对同胞的“劣根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不少文章中予以揭示鞭挞,家中的佣人有没有他所指的“劣根性”呢?她们生于其时,不可能独善其身,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譬如说,愚昧迷信不知求真,把不住嘴拨弄是非等,但鲁迅对她们网开一面,笔下留情,他的文章没有对这一类大字儿不识的“下人”嘲讽挖苦,笔锋触及的往往是当权者或是一些和他有过节的文化人,这不能不说是鲁迅平民观的体现。
- 平潭可建海峡西岸硅谷2015-07-24
- 原住民生活悄然变化2015-07-24
- 海坛古城融入两岸文化2015-07-24
- 台商投资平潭热情高涨2015-07-24
- 辞职看世界女教师情定成都2015-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