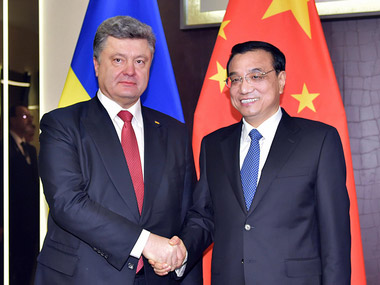夏引业:香港宪制秩序源于国家宪法
文|夏引业
1997年的香港回归,是一场主权性革命,香港的宪制秩序从此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以中国宪法和基本法为核心的新宪制秩序取代了之前港英的旧宪制秩序。然而,基本法实施十多年以来,香港宪制秩序,是中国宪制秩序派生的、次级的,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非完全的独立性的特点至今尚未得到阐明。
基本法是“准宪法”无主权要素
现行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第62条第13项又授予全国人大“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的职权,1990年全国人大据此制定和通过了香港基本法并于香港回归后施行于香港。
香港基本法与其他的全国性法律不同,它无论从立法语言、篇章架构、立法技术,还是规定的内容等各方面来看,都极像一部宪法,它具有一定的宪制性,具有一种“准宪法”的性质。换句话说,如果基本法有效,那么香港将以基本法为基础形成一种“宪制秩序”,但它同时也因此面临违宪性质疑。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下简称“全国人大决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进行了合宪性审查,该决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按照香港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是符合宪法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后实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依据。
现在看来,该决定具有两层意思: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后实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依据”,这就是授权香港以基本法为基础形成一种新的宪制秩序。基本法也因此被称为香港的“宪法”或“小宪法”。第二,基本法“符合宪法”,这一方面释除了有关基本法违宪的质疑,另一方面又说明在以基本法为基础的香港宪制秩序与以中国宪法为基础的中国宪制秩序的关系上,香港宪制秩序归属于中国宪制秩序,香港宪制秩序是中国宪制秩序所派生的、次级的宪制秩序,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中央对港政制发展具主导权
由此可见,基本法是“准宪法”,但不是完全意义的宪法,它欠缺主权的要素,它这方面的不足只能通过中国宪法而获得补全;香港实行高度自治,但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它首先是中国的一个地方单元。
认识香港宪制秩序的此种特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实践中,基本法的“宪制性”、“准宪法”、“小宪法”的性质或地位被不断强调,香港社会也经常称基本法为“宪法”,而其以基本法为基础的香港宪制秩序的派生性、次级性和非完全独立性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可以说,基本法实践中产生的诸多争议莫不与此相关。
在香港回归后不久即发生的吴嘉玲案中,香港终审法院根据基本法授予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推导出自己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的权力。终审法院显然从根本上颠倒了权力的授受方向,它没有看到香港宪制秩序的派生性、次级性和非完全独立性,只有中国宪法凌驾于基本法之上,而不是相反;违反基本法的审查权限于香港的宪制秩序之内,而不能跨越此界限;香港宪制秩序应该纳入中国宪制秩序的框架而不是相反。
这对于刻下启动的第二轮政改咨询也具有重要的提示意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政改决定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香港行政长官候选人必须“爱国爱港”,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政制发展中具有主导权,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香港宪制秩序的派生性、次级性和非完全独立性的要求和体现。
作者为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香港大学访问学者
- 叶太:23条不立 外力“港独”心不死2015-01-23
- 陈健民纵容暴力撕破“和平”假面具2015-01-23
- 廉署追查“黑金”贿赂议员案 黎智英插翼难飞2015-01-23
- 电邮揭陈健民催“占”暴力化 鼓吹仿效日韩2015-01-23
- 中央官员晤反对派 林郑愿安排2015-01-23